一年后的腊月二十八,我跟房东说,这房我不租了。
房东是个胖胖的浦东太太。她当然自己没有过来浦西,而是在微信里跟我说:「怎么啦?小闻,你这么房子,小吴不是跟你交到了下个月中嘛。你过完年可以回来再住一住的嘛……」
我掐掉了房东阿姨的语音。小吴,吴成浩,就是我的前男友小A。这个名字已经在我的人生里,消失了快一年了。我不想,也不爱听到任何人提到他。
「不用了,X姨。我换工作了,我年前就搬走,过完年会租一个离新公司近一点的地方。」我飞快地回复道。房东阿姨,你也不想想,小吴上次交完一年房租后,您还见过他吗?要不是因为穷,我特么早就想搬走了。
是的,我还是很穷。我也没有换新工作,还是在那家坑爹的徐汇律所挂职,还是被外派到漕河泾的一家日企上班,还是一样天天被猪头一样的中村视奸,我还只能赔笑,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
收拾了整整一个下午,但我没有收出来太多东西。因为我准备断舍离,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,我都不想要。学生时代的衣服,有点旧的手包,还有以前发神经买的一堆杂七杂八的心理学书,我统统不要了。爱谁谁吧。
腊月二十八这个时候,也找不到回收杂物的人了。那种一般都和我一样,是外乡人。此刻早早回家过年了。「要不这些东西就留给X姨吧,爱要不要。」我想。
收拾完了,最后我打包就是1个28寸的大箱子加上一个大书包。这些东西我得带回扬中去,然后过完年再带回来——然后重新租房。
我这间财大附近的老公房,是没有电梯的。我只能背上书包,一点一点挨着把大箱子往下搬。那个箱子侧面和正面各有一个拉手,我两只手各拉一边,这样分散下重量。即便是这样,我也只能一口气搬个两楼。而我住六楼。
这真他妈不是人干的活。我心里暗暗地想。虽然是大冬天,我还是搬了一身汗。搬到四楼的时候,我在琢磨,这得亏是往下搬,如果是往上搬,还不得累死?
搬到二楼的时候,我终于想起来,这个28寸的大箱子,上次被搬上楼,是我和吴成浩从山西回来的时候。那会儿天还很热。那会儿我自己一口气上了六楼,留下他一个人搬着这个大箱子。
如果,我是说如果,他还在的话,我一定一定不会让他一个人搬了。我想。
箱子终于被我搬到楼下。随即接到了我妈的电话。
「喂,渺渺?曹倩她们家说今天不回了,三十再回。那你看怎么办?你要不也等三十下午再回,还是……」电话那头,老妈又给了我一个噩耗。
原本按计划,我是要搭一个远房亲戚曹倩她们家的车回老家,扬中市的。路程也就两百多公里。
说起来也离谱,上海到江苏扬中,听起来都很发达的两个地方,没高铁,更不可能有飞机。如果我今天没法搭上车,我要么等她们家,要么只能去坐大巴。
我当然不能等她们。别说我屋子已经收拾得像被鬼子扫荡过一样,就我手头这个28寸箱子,我就没法再搬回六楼。
我当然也不想和农民工去挤大巴。那种车,我读书时坐得多了,一股子酸臭味儿,令人作呕。
我想到了第三种方案。滴滴顺风车。
我掏出手机,准备直接顺风车回家。结果一看,春节期间加价,几乎要五六百的价格。
妈的,抢钱啊。我咬咬牙,后牙槽都快咬碎了,还是屈服地点击了「接受拼车」。算了,生活就是苟且且且且且且~~
出乎意料的,我等了很久。想来也正常,腊月二十八,已经不算很早了。很多在魔都的做生意的,打工的,自由职业者,基本都已经回老家了。只有像我这种坐班的,还拖到了现在。而很多滴滴司机,是属于前者的,他们早就开车回家过年了。
终于,叫到了一辆丰田卡罗拉。七八分钟后,车到了。
司机没有下车,只是开了后备箱,让我自己装行李。我走到车后面,打开行李箱,发现里面烟啊酒啊箱子啊,几乎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。我摆弄了一会儿,勉强把我的书包塞了进去,但是我的大箱子怎么办?
我踌躇了这么一会儿,司机终于下车过来了。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,头发花白胡子拉碴。他瞅了我一眼,又瞅了箱子一眼,说道:「放不哈了,放前头。」
我知道他的意思,「放前头」就是让我放车厢里。我先打开副驾驶门,傻眼了: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两笼子鸡,摞在一起。
不知道从上海往老家带土鸡是个什么思路,我只能打开后排座,又傻眼了,后排座已经有人了,是个肤色有点点黑,年纪不大的小伙子。
我把行李箱横过来往里杵,想直接塞在后排我们两个人中间。小伙子也帮我把箱子往里拽。这时候司机又跑过来了,摇摇手说:「不行不行。则个箱子不能放中间,要倒的。」
他的扬州话我和那个小伙子都听得懂。他的意思是,车子开起来,这个箱子会东倒西歪,倒在我或者那个小伙子身上。
于是在他的指挥下,我先坐了进去,然后箱子再被塞了进来——贴着右边车门放。这样会稳当一点,只不过,卡罗拉的后排本来就窄,我跟那个男生就有点挤了。
车子开动了。果然是晃晃悠悠的,看来司机对于他这辆丰田的地盘有着充分和清醒的认知。
我有点尬,很久没跟年轻男孩挨这么近坐着了。然后,我还得一只手扶着我的箱子,否则倒下来砸我脑门一个包。
一开始出上海倒不是很堵,该走的外地人外地车,这个点都已经走了。但到了京沪高速苏州无锡段,就堵得很了。这两段是城市化高度发达,高速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市内交通要道了,不仅仅是过路车,本地车都很多。再加上「天上飞机,地上苏E」的苏州牌照到处乱窜,我的这个司机又是个慢性子,只知道温吞吞地窝在超车道上,随缘地向前挨着。
我有点急。我性子本来就有点儿急。我说:「欸!师傅,你走右侧道嘛,右侧道,快一点儿。」
司机师傅不紧不慢地说道:「现在这帮小年轻,都不上规矩!都是右边超车!我不着急!我还是走超车道,规规矩矩,安全。」
我气苦,谁特么不知道,高速上超车道是最慢的。这个司机不着急,但是我着急回去啊。于是我回过头来问旁边的男生:「欸~你~你着急吗?」
那个男生吓了一跳,脸涨得通红。他似乎没料到我会跟他主动说话,支支吾吾地说道:「我……我啊?我也不着急的。」
「行!」我牙缝里蹦出来一个字,随即靠在座椅背上,两手叉在胸前,自己一个人生闷气。摊上了两个不着急的主,行,服气。
实际呢,事实证明,我急也没有用。因为很快就堵上了,走走停停,时速不超过10码的那种堵。司机深一脚浅一脚的,很快我就有点晕。然后我就闭上了眼睛,接着我就犯困了。
「嗙!啊呀!」我鬼叫了一声。倒不是箱子倒下来砸着了我的头,而是我犯困,脑门杵箱子的硬塑料壳上去了。那壳还有凸起,一下子把我磕醒了。
我对着箱子发呆:这个箱子现在是竖着放的,近乎垂直。侧倚在上面睡,跟倚在墙角睡,没什么两样。
发呆的同事,我感觉到左侧有目光在瞟我。在这一方面,女生的直觉都可准了。我扭过头,跟那个男生的目光撞了满怀——他果然在盯着我看。
然后我盯着他的肩膀,看了半分钟。他盯着我盯着他的眼神,也看了半分钟。半分钟后,还是他先说话了:「要不……你靠我肩膀?」
我愣了一下,随即二话不说地就靠了上去。我感觉到自己的长发散在他的衣领,胸前,头发顶蹭着他的脸。
不得不说,这个肩膀,就进化得恰到好处,发育得恰到好处,刚好适合我把酸痛的脖子搁上面。
「你哪一年的?」我靠在他肩头,突然嘟囔着问道。
「啊?」
「你哪一年的,多大?」我接着问道。
「啊,我01年的,22了。」
「噢,你01年的啊?」我说道。
实际应该是21周岁吧。可是我们当地的习惯是算虚岁,这个虚岁就真的很虚,有的人加一岁,有的人加两岁。反正按我妈的算法,我虚岁几乎都要30了。
我正胡思乱想,男孩也问我:「那你是哪一年的?多大了?」
我其实是99年的。「女生的年龄不能问,没听说过吗?」我把他怼了回去。
很明显,男孩不仅仅是话头被我怼回去了,连自信和勇气也被我怼没了。他整个人蜷缩着,头低着,想没话找话,却又不知道说什么。
欸我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太好,是该改改了。我想了想,挤出来一丝温柔,问道:「你也是扬中的?哪里啊?」
「我是新坝镇的。你呢?」
新坝?那是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?我有点懵。「我是市里的。那……你叫什么名字?」
「我叫葛帆。你呢?」
「我叫闻渺渺。」我说。
这就是闻渺渺和葛帆第一次认识的故事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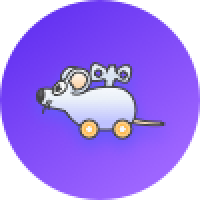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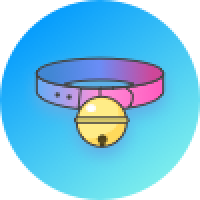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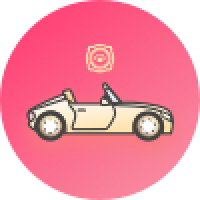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